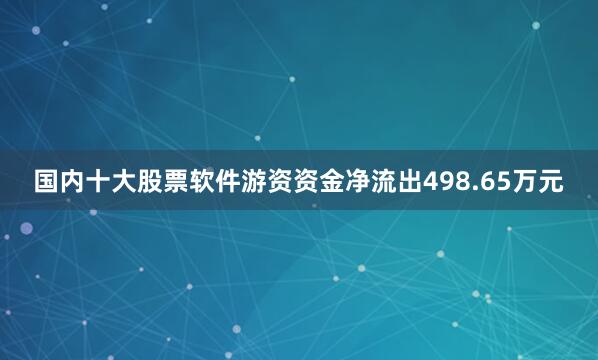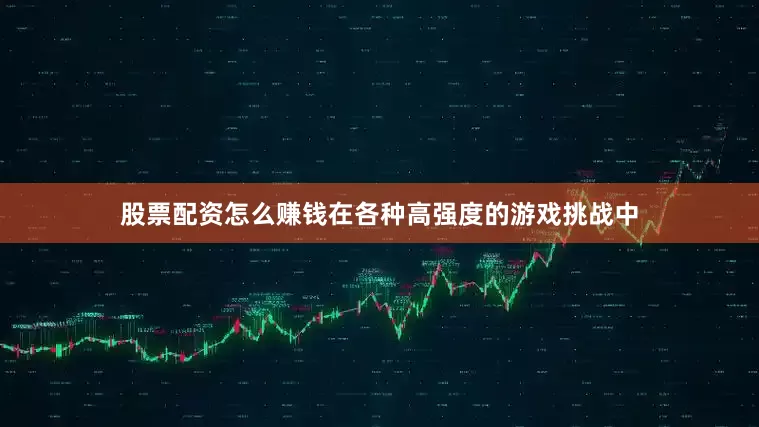《长安的荔枝》首次发表于《收获》杂志2 021年“春卷”后于2022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。
大唐天宝十四载,上林署监事李善德被同僚们联手蒙骗,接下“荔枝使”这顶看似荣耀实则催命的官帽——要在贵妃诞辰前将岭南鲜荔送入长安。荔枝“一日色变,二日香变,三日味变”,岭南至长安五千余里,山水迢遥,这分明是一条由时间与空间共同构筑的死亡之路。
李善德并非不知此任荒唐。然而当真相撕裂,他只能在绝望中攥住一丝微光:“就算失败,我也想知道,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”这一腔孤勇,最终不过是专制巨轮下微不足道的注脚。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,个体命运如同被碾压的尘埃,卑微而无力。
这“不可能完成”的任务本身,便是一面照妖镜,映射出专制体制的荒诞本质。贵妃齿间渴望的那一点清甜,竟需倾举国之力去填满。权力意志的扭曲,竟能将个人口腹之欲,瞬间异化为整个帝国的疯狂律动。这荒谬如利刃,剖开体制的深层病灶:在权力的金字塔顶端,帝王一念,便是天下苍生头顶不可测之雷霆,荒唐亦是天条。
展开剩余72%权力盛宴下的血色果实令人窒息的是,在这架庞大的统治机器中,荒唐从不会遭遇质疑,只会被层层推诿与转嫁。从深宫到岭南,无人敢言“荔枝不可至长安”。权力链条上的每一环,都熟练地将责任如烫手山芋般向下抛掷。李善德,不过是这荒谬传递链条的末端承接者,一个被精心选中的牺牲品。这种自上而下、心照不宣的“替罪羊”机制,正是专制体系维持其病态运转的冰冷逻辑。
这种逻辑在蒲松龄《促织》中早已显现其狰狞面影。华阴县本无蟋蟀,然县令偶然进献的一只善斗之虫博得圣心,竟使岁贡蟋蟀成为定例。于是层层盘剥,成名等小民为觅一虫而倾家荡产。权力机器一旦启动,其碾压的惯性足以摧毁一切理性边界,将个人命运化为齑粉。
其根源在于权力的绝对垄断与等级森严。“黜陟之权,在上台不在百姓。上台喜,便是好官;爱百姓,何术能令上台喜也?”(《聊斋志异·梦狼》)此语如冰锥刺骨,道破专制官场的终极生存法则。在权力金字塔中,官吏的命运悬于上级好恶一线,百姓疾苦不过是遥远模糊的背景噪音。 君权如天,不受制约,官吏权力唯源于上而非源于民。正是这种结构性困境,使得任何理性声音在权力意志面前皆成禁忌。
于是,为了帝王一物之喜,整个社会被强行扭曲、动员。上至官吏,下至黎庶,皆被卷入这场为满足权力顶端私欲而进行的残酷绞杀中。《促织》中,一只蟋蟀能使人“裘马扬扬”,亦能使人“转侧床头,惟思自尽”;《荔枝》里,李善德拼尽性命,只为将几颗可能早已变味的果子送到长安,博贵妃一粲。帝王一跬步,皆关民命;权力一嗜好,便是无数蝼蚁的血泪祭坛。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杜牧的诗句早已写尽这盛世的残酷与遮蔽。红尘深处,是无数驿卒倒毙的枯骨,是沿途州郡被榨干的民脂民膏。
专制权力不仅掠夺物质,更深层地制造着精神的荒漠。在漫长的等级压迫与精神高压下,奴性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毒瘤。民众在恐惧中卑微生存,人性在扭曲中麻木沉沦。如蒲松龄所叹:“天子偶用一物,未必不过此已忘,而奉行者即为定例。加以官贪吏虐,民日贴妇卖儿,更无休止。”
李善德最终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?这已无关紧要。在权力的血色盛宴中,他的挣扎与倒下,只是无数被碾碎灵魂的缩影。那几颗抵达长安的荔枝,早已不再是岭南枝头的清甜果实,而是专制肌体吮吸民髓后吐出的残渣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与《促织》相隔时空,却以相似的荒诞与悲怆,共同奏响一曲专制权力的安魂曲。它们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相:当权力彻底垄断、毫无约束,当个体价值被宏大叙事彻底吞噬,人性之光便在扭曲与黑暗中艰难喘息,直至窒息——这是历史长河中,无数血色荔枝与蟋蟀共同书写的残酷寓言。
发布于:江苏省网上安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